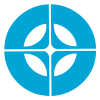從這一期開始,我們推出「台灣宣教之旅」這個新專欄。
追尋、記錄與書寫宣教歷史,是宇宙光四十多年來的異象與負擔,我們責無旁貸。以宇宙光有限的資源,企圖完成這麼大的題目,自然是一個極其艱難的挑戰。然而,兩年來在全省跑透透的田野調查裡,即使我們的視野與心靈不斷受到衝擊,追求的企圖心也一直面臨挑戰,但是帶領我們的,始終是宣教先賢的毅力、勇氣,以及為信仰擺上所有的榜樣。所以,我們終於鼓起勇氣,決心推出這個專欄。
面對台灣的宣教歷史,我們的能力與關照的層面必然極其有限,但是我們依然願意獻上有限的心力與努力,希望能將有關宣教的美好見證,忠實完整地呈獻給所有讀者,因為先賢美好的見證如此激勵我們。
 |
從打狗港開始前進
我永遠記得那個旗津渡輪碼頭的午後。
那天的高雄港灣無比寧謐,大約午後一時許,車抵旗津碼頭,推開車門,一陣冷冽海風撲面而來,仲冬季節,陽光明亮晃眼,風涼天藍,碼頭上正有一艘渡輪靠岸。在腦海中翻閱著資料,我遠眺整個港區,遠處有旗後砲台、旗後燈塔,近處是旗後教會,對岸便是英國領事館,而這裡,是近代長老教會第一個宣教士登陸台灣的地方,他在這裡設立台灣第一間醫館,以及第一間禮拜堂。
雖然曾大量閱讀馬雅各相關資料,但身處真實的場域,面對真實的氣味、真實的建築,那段紙上黑白的歷史,陡然從書冊和史料中一躍而出,鮮活地呈現眼前──我彷彿看到一百五十年前,那個金髮碧眼、帶著滿腔熱血與使命來到台灣的馬雅各(James Laidlaw Maxwell,1836~1921),當他第一步踏上打狗港(今高雄港)時,應該見到了旗後砲台,以及興建中的英國領事館。雖然馬雅各在南台灣的史蹟多不勝數,但打狗港應該是我們的第一步。而追隨馬雅各宣教的足跡,踏查拜訪了許多教會之後,我們追索出一些非常有意義又有趣的歷史聯結,得到極豐盛的收穫。
我們首先想到的是──為何是1865年?馬雅各來到台灣的年代是偶然?是心血來潮?抑或是受到時代影響?其實,馬雅各受到杜嘉德(Carstairs Douglas,1830 ∼ 1877)牧師影響之時,正在英國伯明罕醫院擔任住院醫生。在一次教會的聚會中,遇到從中國廈門回國分享的杜嘉德,那是他第一次聽到台灣。當時馬雅各雖然剛剛訂婚,卻立下心志,離開故鄉,踏上未知的宣教之路。馬雅各辭去伯明罕的優沃工作,剪下一綹頭髮,送給摯愛的未婚妻,以表思念不捨之情。1863年8月,馬雅各與杜嘉德牧師一同搭船飄洋過海,踏上前往台灣的遙遠路程。
就像台約爾(Samuel Dyer,1804~1843)與馬禮遜(Robert Morrison,1782~1834)等先賢的遭遇一樣,馬雅各的來台之路也曲折離奇不遑多讓,且深受當時清朝政治、外交、經濟等條件影響。1864年10月5日,馬雅各與杜嘉德牧師、吳文水以及兩位信徒在打狗港登陸,探尋在台灣宣教的可能,實地考察後,他們認為府城台南的人口遠比打狗還多,最適合作為宣教的起點和中心;考察結束,10月30日,一行人返回廈門。
當時清朝正發生巨大變化,內有太平天國之亂,外有英法兩次聯軍徹底摧毀清朝的國防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,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的簽訂,開啟了宣教士在中國的自由宣教之路;打狗(高雄)開港,對台灣宣教則有著最大助益。在這樣巨變滔天的時代,馬雅各接受上帝的呼召,奮起接棒,終於敲開台灣近代基督信仰宣教的大門。
緊閉的宣教大門終於開啟
1858年,清朝與英法聯軍交戰,又稱第二次鴉片戰爭。戰敗後,清朝與英、法、俄、美各國簽訂天津條約,在對各國的條約中,都有一條與宣教至為相關的條文,分別是:
1.對英法的條約第二條:英法人士可在內地遊歷及傳教。
2.對俄國條約第四條:俄國人在內地傳教,中國方面不得禁止。
3.對美國條約第四條:對於傳教士,地方官當一體保護,他人毋得騷擾,即「寬容條款」。寬容條款的重點是,不僅外國傳教士,連中國信徒也受條約保護。
這些條文保障了宣教士在中國宣教的自由,而有了天津條約的保障,中國緊閉的宣教大門終於打開。
但是,天津條約並未立即執行,因為清文宗奕?不願接見英國與法國新任公使,於是戰事再起,清朝再敗,便有了1860年的北京條約,在與各國簽訂的北京條約中,天津條約內容終於再次獲得確認。
此外,北京條約中還有一條值得注意:增開牛莊、登州、台灣(今台南安平舊港)、淡水、打狗(今高雄)、潮州(後改汕頭)、瓊州、南京及鎮江、漢口、九江為通商口岸。打狗港,就從這個條文開始,登上台灣宣教史的舞台。
在歷史脈絡中的台灣宣教史
當馬雅各決定辭去醫職、確立了自己成為海外醫療宣教士的心志,清朝與各國接續有了條約的簽訂,這是那時候的時代背景。在如此的歷史脈絡中,如果沒有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的明文保障,馬雅各的宣教之行,即使能夠成行,必然充滿艱難與不可測的危險;然而,即使有了法令保護,馬雅各登陸台灣之後,仍在台南遭受群眾暴亂攻擊,不得不在一個月內廢然退回打狗。由此可見,不管在中國,或在台灣,宣教先賢不僅要面對整個歷史環境的挑戰,還要面對地方群眾因文化信仰隔閡,一觸即發的種種危機。
漫步港區,旗後砲台至今依舊傲然挺立,彷彿訴說著對西方文化的堅拒與對抗。馬雅各在1865年設立於砲台下方的醫館與禮拜堂,已經無跡可尋,只能勉強追索可能的地點。眺望港區對岸,英國領事館經過一百五十多年的風雨,如今卻成為遊人如織的名勝古蹟,我們不禁想像:這座與馬雅各登台同一年建立的領事館,在台灣政治、外交與經濟都有相當大的影響;而在1865年,當馬雅各從台南退回打狗,是否曾經受到領事館的保護,才終於能在打狗地區安全立足,從而逐漸開啟他的醫療宣教呢?
歷史的答案很難有明確的定論,但是在歷史脈絡中追尋宣教先賢的腳蹤,讓我們有著無比豐富的收穫,這收穫不只是知識的,更是對宣教先賢的再認識,連結遙遠歷史與腳下土地的關係,以及對上帝的深深感恩。
……(請見2017年10月雜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