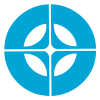|
| ↑一下飛機,黃凱琳一行人就被當地孩子簇擁著前進。 |
「在愛斯基摩人的語言裡,沒有一個字和『戰爭』有關。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,不知道戰爭是什麼、滋味如何──當我第一次抵達蘇丹(Sudan)和南蘇丹(South Sudan),我覺得我就像是愛斯基摩人一樣。」
2016年秋天,長期服務於南蘇丹的美國宣教士金柏莉.史密斯(Kimberly L. Smith)來台演講。十年來,她所創立的非政府組織「開路夥伴」(Make Way Partners)致力於當地人道工作,設立學校、孤兒院、教會和診所,服務範圍包括最危險的內戰前線努巴山脈(South Sudan);即使自己曾遭當地阿拉伯民兵性侵,仍堅持這些工作至今。
她受邀於媒體平台「世界微光」講座演講當天,碰上颱風來襲,卻吹不散許多台灣青年的熱情。當晚,台下兩百多位眼神炯亮的年輕人,專注地聆聽金柏莉所看見的一切;其中一個二十三歲女生的未來,更從此起了改變。
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,至今內戰不斷
位於非洲的南蘇丹,主要族群為丁卡族和努爾族,官方語言為英語,通用阿拉伯語和部族語言,多信奉原始宗教,少數百姓為穆斯林和基督徒。2011年,南蘇丹從蘇丹獨立,成為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,也是最貧窮的國家之一,更和敘利亞、索馬利亞、伊拉克、阿富汗同為全球前五名最危險的國家。至今,南蘇丹和蘇丹交界仍然戰事頻傳,內戰也從未間斷,目前已超過百萬難民流離失所。
南蘇丹七成國民是文盲,雖然國內現行小學八年、中學四年、大學四年的義務教育,但教育水平低落、教學資源缺乏,小學就讀率大約三成,大學註冊率僅千分之二。然而,在求生為先的情境下,人民光是與貧窮、轟炸、野獸或氣候搏鬥已無餘力,更不用提下一代的教育。
「村莊被集體攻擊,父母親眼看見女兒被軍人性侵、殺害;遭受惡待的婦女身體殘缺、發出惡臭;在努巴山脈,人們只能藏在洞穴躲避飛彈,過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只有一天沒有爆炸聲。」金柏莉緩緩說著她所看見的南蘇丹:「孤兒在荒漠和叢林中漫無目的地行走,找不到食物的時候,只能吃樹皮,晚上,他們睡在大樹上躲避野獸攻擊,如果不幸掉下來,不是摔死,就是被鬣狗咬死……」
「我憑什麼出生在台灣?」
「我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故事,讓坐在台下聽演講的我聽到受不了……」當時任職於世界展望會的黃凱琳,對於世界各地的苦難和困境並不陌生,但當她得知南蘇丹所發生的一切,仍震撼得無法言語。
長期以來,許多跨國NGO的援助工作都無法進入南蘇丹,因為該地情勢極度不穩,幾乎無法建立任何長期計劃。在這個國家,擁有任何職位或國籍都不等於擁有保障,聯合國團隊被攻擊,國際志工與外籍記者被搶劫、性侵、殺害的案件,時有所聞。
「但那場演講後,我卻一直想著:『為何我們幫不了這些孩子?』『為什麼做不到?』」在黃凱琳心中,浮現一張名為〈飢餓的蘇丹〉的照片,一個骨瘦如柴的孩子蜷縮著身體,而一隻禿鷹正在背後等著孩子死去,「這張照片攝於1993年,我正是1993年出生的,我不禁問自己:『憑什麼是我出生在台灣,而不是那個孩子?如果我出生在南蘇丹,我現在的命運會如何?』」黃凱琳心中浮現一個聲音:「你是不是應該再多做點什麼?」
她私下聯繫金柏莉,正好金柏莉希望在台灣成立機構據點,便邀她加入團隊。「但我還在猶豫,便回答:『如果最後還是沒人,再來問我吧!』當時我心想,熱血青年這麼多,一定會有人願意的。」沒想到,金柏莉離台那天,黃凱琳接到金柏莉從機場打來的電話:「凱琳,最後還是找不到人,你來吧!」
於是,黃凱琳就這樣成為「開路夥伴」唯一的台灣正職員工。向世界展望會辭職時,主管大方鼓勵她:「凱琳,這件事真的很棒,我覺得你是適合的人選!希望上帝帶你到影響力更大的地方。」黃凱琳說:「當時,我想像中發揮影響力的方式是,在台灣『蒐集新聞』、『翻譯南蘇丹資訊』、『坐在辦公室處理行政事務』……,沒想到,一個月後,我就親自去了南蘇丹。」
第一次走進南蘇丹的震撼教育
原來,「開路夥伴」在南蘇丹建立了三間學校,其中一間位於西北方、名為Nyamlel的小村莊,是最早開始、設備最完整的學校。2016年年底,這所學校即將迎接第一批高中生畢業,雖然只有十六人,卻是當地難得的大事。
 |
| ↑小學的朝會集合。 |
「在求生第一的環境下,沒人敢期望自己能就學,更不用提『高中畢業』,但在Nyamlel的這間學校,有小學、國中到高中的完全中學,有從孤兒院演變而來的學生宿舍,有類似保健室的診所,有一間小教會,有鐵絲網與配槍的警衛保護,更有全南蘇丹唯一的電腦教室。全校七百五十位學生都是『開路夥伴』收容的孤兒,許多人都是整個家族中唯一識字的成員。」而黃凱琳的任務,就是去見證這場畢業典禮。
從台灣搭機到烏干達,再從烏干達坐小飛機到南蘇丹首都朱巴(Juba),最難熬的是搭乘小飛機的過程中,不只需要降落兩、三次加油、轉機,還得忍受不穩定的氣壓與劇烈搖晃;來回耗上二十多個小時,讓她嘔吐到連膽汁都吐了出來。抵達目的地,「機場」是沙漠中的一塊黃土硬地,住的是帳篷,洗的是發臭的黑水,每天的飲用水都必須加幾顆維他命發泡錠「緩和」味道,沒有電話與網路,只能用機構的衛星電話對外聯絡。第一晚,黃凱琳聽著整夜野狗跟鬣犬的吠聲,徹夜難眠。
「我想起那些學校無法收容、仍露宿樹上的孩子,『他們睡在哪裡?』『今晚安全嗎?』『為什麼學校不能收更多小孩?』想著想著,大約凌晨四點多,我聽到一個孩子淒慘的尖叫聲,卻分不出那是男孩女孩,也不知道那是被野獸攻擊還是從樹上掉下來的慘叫聲。」她回想:「我躺在帳篷裡,開始一直掉眼淚,多麼希望那個孩子可以安全地睡在我身旁……」
……(文未完,請見2017年2月雜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