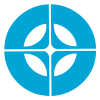|
| ↑普林斯頓一畢業,蘇奕安就搬到中東。 |
2014年12月,年僅二十七歲的約旦飛行員卡薩斯貝(Muath al-Kassasbeh)遭伊斯蘭國(ISIS)擄作人質,成為伊斯蘭國與約旦談判的籌碼。談判最終破局,2015年2月,卡薩斯貝被關在牢籠裡活活燒死,伊斯蘭國在網路上公開這段影片,震驚全世界。
卡薩斯貝出事後,許多人聚集在他家慰問和哀悼,在一片群情激憤的約旦人潮中,有一個東亞面孔的長髮女生在其間穿梭。她是蘇奕安,二十五歲的台裔獨立記者,待在中東已兩年。卡薩斯貝一家服喪的三天期間,她都在現場。
當我和「聖戰士」的家人在一起
「飛行員出事前,約旦國王宣布加入西方反恐陣線,很多約旦人都對這個政策持保留態度,不想親近美國;因為如果有個萬一,倒楣的是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隔壁的約旦,而不是遠在天邊的美國。直到卡薩斯貝出事,全約旦陷入激情,我搭計程車時,司機甚至一邊哭一邊對我說:『伊斯蘭國簡直不是人,他們根本不是穆斯林。』」
伊斯蘭教法裡,穆斯林不能殺穆斯林,如果做出這樣的事情是大罪。對極端組織來說,他們自認信仰最純正,其他人都是異教徒,因此合理化大屠殺的行為。但是,一般穆斯林沒事不會宣稱別人不是穆斯林,因為他們認為那只有真神才能判斷,如果出現這樣的狀況,代表情勢極度不尋常──就像此刻,約旦飛行員死了,全國大街小巷的電視、廣播、新聞報紙和政府,都在吶喊「伊斯蘭國不是穆斯林」。
「服喪第二天,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(Abdullah II Bin Hussein)來了,他說卡薩斯貝不只是伊斯蘭的shahid,也是約旦的shahid。」「shahid」,意思是烈士、見證人,不是所有死去的穆斯林都能成為「shahid」,而是為了伊斯蘭、為了崇高的信念而死,才能稱為「shahid」。「國王在台上發表宣言,卡薩斯貝的父親站在他身邊,台下一波波年輕人不停向前簇擁,大叫著:『我們也要當shahid,派我們去開飛機,我們要殺死那些人!』在他們頭上那片天空,則掠過一架架飛機,他們是卡薩斯貝的飛行員夥伴,準備前往伊拉克和敘利亞報仇。」
「大家都很激動,但只有兩個人不贊同卡薩斯貝是shahid,就是他的妻子和妹妹。」
我不要我的家人是Shahid
正當國王和群眾在外群情憤慨的時候,她們倆坐在家裡,仍處於失落和心碎之中,親友圍在她們身邊安慰:「感謝真神,卡薩斯貝成了shahid,現在已經上天堂了。」她們卻聽不進去,不停說:「不要說他是shahid!我不想聽到他是shahid!」
卡薩斯貝的妻子告訴蘇奕安,她的丈夫很善良,也是虔誠的穆斯林,每天早上開飛機前,他都會很早起床,特地為出任務禱告:「神啊,請不要讓我殘殺無辜的人,尤其是穆斯林孩子。」身為飛行員,卡薩斯貝似乎也不是很確定自己為何從事這樣的工作,他不想打仗,也不知道敵人是否真的邪惡,但這是他的職業,沒有辦法。卡薩斯貝的死帶給妹妹很大的打擊,後來她看到日本記者後藤健二遭斬首的影片,精神狀態更不穩定,「晚上她去廚房,打開櫃子會隱約看到那個日本人的頭在裡面。半夜睡覺睡到一半,她會突然起床跟姊姊說:『姊姊,我覺得那個日本人的頭在我床底下。』」
服喪期間,蘇奕安坐在一旁,看著這兩個女人互相安慰。「當她們安慰彼此的時候,不是說『還好,卡薩斯貝是shahid。』而是說:『那個影片看起來很假,肯定是電腦偽造的,你是不是覺得他還活著?』『對!我覺得他還活著。』」
卡薩斯貝的妻、妹,讓蘇奕安想到另一位shahid的母親。
我的家人是Shahid
吉哈德(Jihad Ghaban)騙母親自己要出國旅遊,實則跑去敘利亞加入激進組織。一開始,他只是幫忙組織拍照、寫報導,上傳到社群媒體,漸漸的,他的發言越來越極端,臉書大頭貼也從「自由敘利亞」(Free Syrian Army)改為伊斯蘭國的黑旗,一年後就加入軍隊。
吉哈德從小就非常有正義感,八歲時,他看見路邊有人在虐待動物,就跑去對大人說教;成年後,他仍然看不慣不公不義,於是參與阿拉伯之春,並在校園發起改革,要求學校幫助貧困學生,卻雙雙得到失望的回應。當時,他在約旦街頭留下一句塗鴉:「為什麼國王活在皇宮裡,人民卻因貧窮而死亡?」吉哈德的朋友對蘇奕安說,吉哈德是他們之中最真誠、最熱心的,但誰都沒想到,他最後會被激進組織吸收。
朋友在吉哈德的臉書留言,希望他返鄉,他卻回答:「你們都沒有作為,而我至少採取了行動。」每週,吉哈德都會打電話回家報平安,他的媽媽也不停勸他回家,直到某一天,她在電視報導恐怖分子的身亡名單時,看見兒子的照片。
「在我面前,這位母親反而一直強調兒子是shahid,他是為了正義才加入極端組織。」蘇奕安說:「我是記者,所以我想知道真相,也想了解她的神學觀念,便一直問她:『但是約旦穆斯林都說這些極端組織不是穆斯林,甚至是異教徒,你怎麼確定吉哈德是shahid?』」
「問到一半,瞬間,我發現自己不該再問了,因為她突然抓住我的手,哭著說:『他是shahid,我知道他是。』那一刻,我發現自己不只是記者,她也不只是一位受訪者,她是一位母親,她很傷心。」
 |
| ↑身為華人,蘇亦安希望自己可以成為東亞和中東之間的橋粱,「華人想到中東就是戰爭跟沙漠,中東人想到中國就是成龍跟便宜的產品,更不用說台灣了。」 |
 |
| ↑難民不只來自敘利亞,還有伊拉克、蘇丹、巴勒斯坦……等地。圖為逃到約旦的蘇丹婦女。 |
蘇奕安畢業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,她說:「當我還在學校、身處在菁英環境中,我覺得世界很簡單,認為自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,直到我去中東,才體會問題有多麼複雜,他們的故事絕對不是黑白分明的,而且充滿各種難受、難堪的悲傷,而我在這些故事裡是多麼渺小。
在普林斯頓看見中東,「發現自己很無知」
成長過程大致平順,蘇奕安形容第一次在學校認識中東世界時「發現自己很無知」。由於父親從事貿易,她從小就在美國、台灣、香港和中國之間來去,因此對中美關係特別有興趣。原本想專注研究中美關係,卻碰上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,教授突然開始談論中東國家。
「大二時,我修了一門國際新聞課程,老師是《紐約時報》駐開羅的記者,他談到茉莉花革命,為什麼這些人要起義、要自由,又看見監獄裡有人遭受虐待、毆打……當時我就覺得自己很無知。談到埃及,我只知道聖經裡的埃及,好像有十災、法老王和金字塔,可是穆巴拉克是誰,為什麼我都不知道?」大二暑假,她就去摩洛哥,開始學習阿拉伯文、伊斯蘭政治和中東歷史,發現西方角度下的中東觀點相當偏頗。畢業後,她搬到阿拉伯國家,第一年在阿曼(阿曼蘇丹國,Sultanate of Oman)學習語言,第二年搬到約旦首都安曼(Amman),大家都對她的決定感到不可思議──其實在她心中,若說完全沒有掙扎,也不是事實。
「我畢業前三週還在想是否該取消機票……」蘇奕安說:「我一直很想待在中東世界,但我其實不是很喜歡那樣的環境。我在摩洛哥不但食物中毒,走在路上還一直受到騷擾,你一定要穿長袖,也不能一個人行動,我不喜歡這麼封閉的社會──而且,前往中東時,我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,也沒有收入來源。」
當時朋友問蘇奕安:「你要去約旦?找到工作了嗎?」她回答:「沒有,但我想先去實習,看能不能找到工作留下來。」
蘇奕安回想:「他們覺得不可置信,為什麼一個普林斯頓畢業生要這樣?」
在穆斯林國度,重新認識福音
初抵中東,有一陣子蘇奕安特別不想提到福音,「除了不想讓我的穆斯林朋友尷尬,也因為我看見許多虔誠的穆斯林過得很好、很幸福,甚至比許多基督徒善良;又有一陣子,我不想相信任何神,因為在中東,我看見所有的民族與國家打著神的名號互相殺戮,如果我的上帝也是那樣冷酷、看著人們自相殘殺,我該怎麼愛祂呢?」後來,她讀到聖經中幾節經文:「『我來本不是召義人,乃是召罪人。』(馬太福音九章13節)、『因為上帝差祂的兒子降世,不是要定世人的罪,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』(約翰福音三章17節)我看到這些經文,好像鬱悶很久的人突然呼吸到一口新鮮空氣。」她回憶:「當所有人都堅持『我是正統的,你是異教徒,所以我要殺死你』的時候,卻只有耶穌說:『你是異教徒,你不相信我,所以我要為你捨命。』我覺得自己好像重新認識了福音。」
當時,蘇奕安一直在思考,為什麼身為Shahid對穆斯林這麼重要?為什麼他們必須不斷強調伊斯蘭國不是穆斯林?為什麼他們害怕自己的家人被歸類為異教徒?又為什麼不能主張各自追求信仰、相安無事就好?「原來,在伊斯蘭世界觀裡,穆斯林有真假穆斯林之分,只有真主能判斷真假,而那個真主,並不愛世人,所以人們很怕自己是假穆斯林。在伊斯蘭信仰,沒有那種可以覆蓋所有人的恩典,穆斯林必須不停質問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;但耶穌說我們全是罪人,只有祂為我們捨命的愛能拯救我們。」
「當我面對穆斯林和各種恐攻消息,現在我都會想:『耶穌會怎麼做?』面對異教徒,耶穌不是以上帝之名將他們趕盡殺絕,而是為他們捨命,當我明白這點,很多問題都不再令我困惑了。」
……(文未完,請見2016年6月雜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