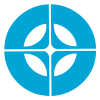|
| ↑三坪大的空間,有時會擠到四十人。 |
三坪的空間,擠了四十多人,大多是小孩,從兩歲半到十四歲都有,轉身都顯困難,雖是寒冬卻絲毫感覺不到寒冷,這是Sunny在印度德里的小客廳。「說是客廳,其實是小房間,我家只有兩房、廚房、浴室和一個小玄關,一開始才四、五個小孩。」
孩子來做什麼?「他們對外國人好奇,常常跑來我家。我在牆上貼了世界地圖,教他們認識國家和城市,有時讓他們讀書、畫畫、看影片,後來還在陽台掛個板子,教他們簡單的中文。」久而久之,變成了每週一次的兒童聚會。
從台灣基層到印度基層
Sunny是台灣平埔族西拉雅族(Siraya)後裔。西拉雅族多分布於台南一帶,有人說,台灣的歷史從台南開始;「台灣」二字的歷史,則可從西拉雅族開始──早期,西拉雅原住民將安平稱為「Tayuan」,翻為「大員」,後來才漸漸演變為「台灣」。
「我家祖先原本是『尪姨』(靈媒,通常由年長女性擔任),到了漢化和荷據時期,全家族成了大地主、基督徒。」自一百五十年前起始的台灣長老教會歷史,還留有Sunny家族的記錄,到了日治時期、國民黨政府來台,家中土地逐步被徵收,父親工廠因親戚倒債而關閉,「家裡突然變得很窮。」
為了還債,Sunny父母帶著三姊弟舉家搬遷,父親得離家分別討生計,母親辛苦帶著三個小孩,有時下一頓飯在哪裡都不知道,「那時我才十歲,心中卻很清楚一件事:教會沒人為我們挺身而出,還欺負我媽媽。」當時大部分教會會友都是家族親戚,卻一個個落井下石,激起十歲小女孩心中一道道漣漪,帶來反覆迴響的聲音:「如果這個上帝是真的,為何發生這種事?基督徒平時的樣子為什麼和禮拜天這麼不同?」
漣漪慢慢擴散,慢慢發酵。在學校,Sunny遭受霸凌,到處跟人打架,姊姊總英勇為她出面,「她是學校風雲人物,每次運動會都會閃亮亮打破自己紀錄的那種;我則是從小體力差,再請假一、兩天就會遭退學的那種。」在校受人欺負,心中憤懣,回家面對姊姊,心生自卑,女孩的自我形象愈來愈低落。
迎接青春期的時候,家裡債務解決了,爸爸回家了。家庭接連遭變,Sunny的父母反倒從有名無實的基督徒成為熱心認真的信徒。「他們認為,要不是有上帝,他們沒辦法度過難關。」但她看盡人情冷暖,討厭教會,更討厭這個世界,「我感到這世界很虛偽、很沒意思,人與人的緣分只是彼此利用的關係。高中畢業後,我開始工作,薪水和職位都跳得比別人快,也有男生追求。但我心中很黑暗,沒有出口,從小累積的比較心、自尊低落,別人都看不出來,以為我很正常。」
青春正好的雙十年華,Sunny決定自殺。第一次跳海,碰上演習被發現;第二次割腕,被人撞見而失敗。走到盡頭,無計可施,「我向上帝禱告,若你真是聖經寫的那個上帝,必定對一切瞭若指掌,若你能改變我,我就把自己交給你。」當下,有東西觸動了心靈,「我竟突然領悟,父母對我好,我視而不見;別人關心我,我扭曲他們的動機。原來我痛苦的癥結點,是我沒有被愛的能力。」
學會被愛,原來就能同時學會愛人。她接連就讀兩間神學院,童年經歷在她心中生成對基層的關懷,自此傾瀉而出。實習時,因不習慣白領階級教會而轉到基層教會,2004年,Sunny到南非半年,在當地接觸到印度人,隔年就踏上印度,待了一個月。
 |
| ↑歡慶印度三大節慶之一的色彩節(Holi)。 |
「對印度的第一印象其實並不舒服,那時的機場又吵又髒亂。」Sunny坦白回想:「我在印度教聖城納瓦拉西(Varanasi)目睹恆河旁的黃昏祭典,每個河壇都站了約一萬人,我深深被震撼。又參觀伊斯蘭區的清真寺,從塔頂往下望,映入眼簾的盡是雜亂……。和台灣差異這麼大,我不禁懷疑,自己真的適合這裡嗎?」她想知道答案,2007年又赴印度學語言半年,2009年再次前往待了兩年,接連接觸村落、鄰居、貧民區,一次次試水溫,最後,終於踏向恆河的國度。
種姓階級的束縛
從台灣基層到印度基層,西拉雅的女兒,成了基督教宣教士,在南亞大陸落腳。2012年,她住進一個勞工社區,是當地唯一的華人;大家對她好奇,從巷頭到巷尾,路人常投以注目眼光,小孩則膽大進門探索,回家後談論外國人的家哪裡長得不一樣。每天同樣的話題,可以持續一個月。
「全社區同屬一個種姓階級,中心思想是『有沒有吃飽』,有時絞盡腦汁思考如何貪小便宜,人生已經沒有其他問題更重要了。」一棟棟樓房,中央是天井,每層六戶人家,需共用兩間廁所。一天,水會來兩次,要隨時準備大小瓶罐儲水。「大家常為了水吵架,嘰哩哇拉吵了半鐘頭、一小時,突然有人喊聲:『飯煮好了!』」Sunny生動形容:「嘩!再大的爭吵都能瞬間鳥獸散。」
印度擁有享譽國際的科技、電影娛樂與軟體工業,同時卻有一半人口生活在極度窮困的環境、以及種姓制度的束縛下。種姓制度分為「婆羅門」(祭司階級)、「剎帝利」(貴族階級)、「吠舍」(工商階級)和「首陀羅」(基層勞工),還有不被當人看待的「賤民」。近年來,許多賤民階級的人為逃離種姓制度改信基督教,以致激怒印度教部分激進分子,限制宗教自由的聲音也日漸增多。
Sunny認識Sonia時,她才十五歲。「有天到她家拜訪,大人都不在,她突然問我可不可以讓她男友打電話給我,我問為什麼,她說:『如果打到我手機,爸爸會看見。男友階級比我低,如果爸爸知道了,會把我們兩個榮譽處決。』」後來,不到十七歲,Sonia就嫁給爸爸安排的對象。
渴望改變,但除了女人
社區居民普遍家境匱乏,寄望教育可以翻身。私立學校門檻高、學費高,公立學校便宜,老師卻不靠譜,折衷之下,父母紛紛送小孩去補習。
經濟雖然拮据,父母栽培子女的心不減,但只有「望子成龍」,沒有「望女成鳳」──女兒的學費總會拖久一點才繳付;男孩出外玩耍時,女孩要負責家事;不吝嗇讓女兒受教育的家庭,理由多是「未來可以找到好夫家」,原來,知識的功能是充當一部分嫁妝。
華人婚嫁習俗裡的「嫁妝」,是印度女人一生的重擔。嫁妝的豐厚與否,不但關係雙方父母的門面、家族地位,更決定媳婦在婆家的待遇。Sunny說:「我參與的當地教會教導信徒彼此相愛,不要把難擔的擔子放在別人身上,但還是很難公開倡導嫁妝觀念的改變。」
其實,光是看見Sunny一個女人獨居,對居民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。Sunny知道這裡的女權問題根深柢固,記錄轟動全球的公車集體性侵案電影《印度的女兒》,就活生生呈現了印度女人的噩夢,連同為女性的母親都可能成為家庭結構共犯的一環;然而,改變並非一蹴可幾,母親這個角色本身也背負許多重擔,或許,先走進當地人的內心,是最好的開始。
……(文未完,請見2017年6月雜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