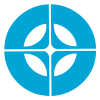|
| ↑2012年袁樂民長老第三次個人書畫展,與宇宙光同仁合影,左二為本文作者張曉風。 |
難得的「同誌」
我和袁伯伯──我這樣稱袁樂民先生──之間的關係既不是同鄉,也不是同學、同事,而是「同誌」。
怎麼說呢?因為我們都曾經向同一家雜誌投稿,這件事,說來話長,已經是六十年前的事了。那家雜誌叫《燈塔》,位在香港,地址呢,我至今記得,是九龍界限街144號。
這本雜誌後來停刊了,雜誌辦著辦著就停了,這事很正常。百分之九十的雜誌撐不過五年,能熬過十年、二十年是變態,是不正常,是奇蹟。不過,《燈塔》停刊畢竟是件憾事,原因是《讀者文摘》出現,搶了市場,訂戶於是銳減,根據市場投資報酬率的原則,支持者便很「正確」地關了這家雜誌社。但我認為,支持者關雜誌之事有點像國民黨關《中央日報》,是省了銀子垮了門面的敗筆。
曾經,我跟袁伯伯是一同耕作的園丁,一起執戈的戰士──在同一本雜誌上。雜誌既是「香港製造」,台灣作者便不是很多,所以我二人算是難得的「同誌」。唯六十年來,他在宜蘭,我在台北,見面不容易,大概不會超過十次。
什麼才算傳奇?
雖然,和袁伯伯不常見面,但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「傳奇人物」。
 ↑袁樂民長老不但是好老師,也是「文」、「書」、「畫」三絕的文化人。 |
「傳奇」二字由唐人小說開始用,後來也用於戲劇方面,但不管是《崔鶯鶯》或《牡丹亭》,其情節在我看來都只是個人戀愛的小事件,談戀愛沒啥稀奇,對古人來說也許罕見,但以今人觀之,等閒小事耳。至於女主角杜麗娘死了又活了,奇雖奇,但因為既是虛構,就無所謂「奇」了──凡不是事實的,哪能算傳奇?彼得潘會飛,這算什麼奇?
倒是民國初年出生的那一代人(用台灣流行的話說,他們是「零年級」或「一年級」的),只要活下來,好像都不免是一則傳奇。
他們那一代稍早的人或經過辛亥革命,把五千年的帝制作了個大翻轉,辛亥革命本身還好,從戰爭規模言,死的人不算多,黃花崗也不過死七十二人,加上無名死者,也不會太多人──我這樣說,好像有點冷血,但相較於抗日戰爭,幾十萬、幾百萬乃至幾千萬的死法,算是情節輕微的。之後是北伐派系之戰,加上中日之戰和國共之戰。能在那日復一日的槍林彈雨中僥倖活下來,只能說是叨天之幸──照我看,這,才算傳奇!
袁伯伯如今九十五歲了,如果要說死亡,他可能「該」死了好幾次了。生於民國十一年,北伐他沒趕上,但抗日之戰的大小四萬次戰役中他參戰了六次,其中一次幾乎全軍覆沒(因為日方施放毒氣),袁伯伯居然在長得高高的麥田中匍伏前進兩公里,得以大難不死。
袁伯伯的戰場都在山東的西南一帶(離曲阜和台兒莊都不遠,啊,想起來了,那附近還有一個縣,名叫「荷澤」,天哪,真是美到令人戰慄的地名,讓我不勝神往),那時是民國二十七年,他,不算正規軍,十六歲的大小孩,是游擊隊戰士。打仗,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家鄉,和鄉人。
之後,他考入憲兵,袁伯伯是身高一米八的北國男兒,很帥氣。
但國共戰爭中,他卻是由雲南翻山越嶺,經法屬越南的富國島,在民國四十二年才到台灣(其他大部分的東南戰區逃難者是三十八年就到台灣了),途中最可怕的是,不但沒什麼可吃的,連乾淨的飲水也沒有,荒莽中,日日有人死於痢疾或傷寒,袁伯伯一行三人,在三天之內喪弟又喪妻,自己也差點死掉。
「義結金蘭」,和人世
到了台灣,又發現了二期肺病,他當時的偉大奢望是願自己能拖到六十歲──不料,上帝讓他活到九十五歲仍然神清氣爽。
袁伯伯前三十年身在赤縣神州,老家是山東金鄉縣,後半輩子住宜蘭,這兩個地方合起來是「金蘭」,「金蘭」是個好詞,袁伯伯和此滔滔人世「義結金蘭」。
袁伯伯後來經由高考而執教中學(其實,由於戰爭,他沒有正規的學歷)。他教美術,是個好老師,也是「文」「書」「畫」三絕的文化人。政客常喜歡把「愛台灣」掛在嘴上,其實說得太膚淺了!為人最重要的是「心中有愛德」,如果沒有高尚的「愛能力」,如何懂得愛台灣呢?其次,光是「愛台灣」是不夠的(這種「嘴皮子的愛」太廉價了),真愛台灣就要努力「把台灣變成人見人愛的好地方」才對──袁伯伯一生就是經由信心、愛心和用功,把自己提昇為「傳奇人物」的。
台灣能有這樣的人,這樣的人能有台灣,都只能說是天恩,袁伯的生平是一部亂世傳奇。
後記:香港《燈塔》停刊,原編輯劉翼凌先生遠遷美國。六年後,他心有不捨,不知如何弄了一筆一千美金的捐款(據說是書法義賣得到的錢,捧場來買的好像是他從前在香港教過的神學生),跑來台灣,想拉人辦一本《宇宙光》雜誌,手捧一千美元就想來開辦一本雜誌,怎麼看都像「傻瓜的傻念頭」,奇怪的是,居然也有傻瓜答應了他(而那一千美金在第一期就用完了),這就是《宇宙光》的上古史。「宇宙光」至今撐了四十四年,我和「袁同誌」又有機會偶然在同一本雜誌中共事了。
……(請見2017年9月雜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