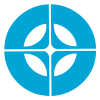光譜同工葉子來邀稿,不加思索便一口答應,因為宇宙光惠我良多,橫跨「兩個世紀」及家中「兩代」。太誇張了吧?不,且讓我細細道來。
話說上個世紀的一九七九年,一位傻傻楞楞的、連國語都講不清楚的香港僑生,因著當年政府僑務與教育政策,很幸運地(信主後知道是神的眷顧與引導)考上了台大外文系,然後不知誰的「耳語」,說台大對面有個「我們咖啡屋」,然後不知怎樣,也忘了當年花了多少錢,忽然間我便到了這咖啡屋,喝著咖啡,做著我的文學夢、作家夢。
那些年,可是王尚義《野鴿子的黃昏》、卡謬《異鄉人》當道的年代,在似懂非懂的存在主義中,外文系的同學都在學習如何在「荒謬」與「意義」中找尋自我存在的座標;外在大環境是中美斷交不久,執政者鼓勵大家莊敬自強,處變不驚;個人小宇宙則是陪著我長大的外婆剛去世。
「人會死,且他們活著也不快樂!」(Men die; And they are not happy!)這是卡謬在《卡里古拉》中的名句,亦是當時最真實的感歎。
就是在如此的渾沌氛圍,若沒記錯,我在「我們咖啡屋」靠近窗戶的一張大大沙發中(第一次坐那麼舒服豪華的椅子),第一次拿起宇宙光雜誌來看,沒想到這一看,便開始了與宇宙光三十多年的關係。
說實在,已忘了當年的《宇宙光》長什麼樣子,有什麼內容,但隱約中,我似乎感受到有某種「光」,透過不同的作者、文章,在字裡行間,引導著我。
很可惜,我們咖啡屋不久便結束了,但與宇宙光的關係卻延綿至今。
剛開始是以讀者的身分來參與,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梁燕城老師的專欄,後來編成《會通與轉化》一書,我們還與一群弟兄姊妹組成讀書會來研討;還有曾慶豹老師的專欄,讓我對一系列的哲學家也有了更多的瞭解。當然,這些年還有許多很好的專欄及封面故事,幫助我在信仰及各方面的成長。
忘了什麼時候及為什麼,有一次,到了宇宙光在新生南路(今大安森林公園)的日式房子辦公室,才瞭解真的「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。」(這「吾」,是指宇宙光的同工啦)反正,那些年,常常知道宇宙光有財務需要,但神總又是適時供應,我知道這真是信心的服事與功課。
還記得當年仍在大光服事,因為創辦《飛越》雜誌,整個機構也陷入沉重財務困難時,一次早禱會,大光的林哥(三民),拿著宇宙光的林哥寫的緊急募款信,問大家覺得如何。其實那正是宇宙光的信心榜樣,一路激勵著我們,才勇敢地辦了《飛越》。若我沒記錯,當年大光為宇宙光奉獻了一萬元(或是五萬元?抱歉實在年代久遠!)。那是一九八七年前後的事。提這,只是想感謝宇宙光的同工,您們的堅持與擺上,其實是不斷地激勵著許多弟兄姊妹。
後來,我不時的為宇宙光寫文章,也參與編輯會議,擔任過編輯顧問,更是瞭解在有限資源與非常緊縮的人事編制中,如何維持雜誌的不斷更新,實在是很不容易的,我真的為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同工獻上感恩。
前文說到「兩代」,那是因為我們家的孩子,一直都很喜歡看《宇宙光》,尤其當我們到了香港、中國,以至現在在墨爾本事奉,每次收到雜誌,搶著拆封套的,都是孩子們,而宇宙光就成為我們在家教育的最重要閱讀教材之一。
若主耶穌沒很快回來,我禱告,到我孫子那代,仍然能繼續成為宇宙光的讀者。我也盼望宇宙光能透過現在更多元的事工,繼續不斷「光」照一代又一代在尋求意義的年輕人,以及一個又一個的家庭。
*作者曾擔任《飛越》雜誌主編、衛理公會台中衛道堂牧師、台灣浸信會神學院專任講師、浸信會「國際」出版社社長、現任墨爾本華恩堂主任牧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