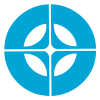接受裝備訓練進入歷史文化、思想領域
研究所畢業,神帶領我進到學校,又以老師的身分來關心文化、關心歷史的問題,我清楚知道我要在中國歷史的傳統中事奉主,我也知道中國歷史文化的根源是在臺灣,於是就許下一個心願,我說:「神啊!我就定在這個地方來事奉。」
我們那個時代,正當存在主義思想瀰漫全球的高峰時期,卡謬、沙特、尼采、貝克特、海明威等人,以文學、哲學的形式深入了台灣整個學術文化思想界,強調一切都是空無,沒有意義,沒有盼望,再加上尼采「上帝已死」的觀念,瀰漫籠罩了整個思想界。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Time雜誌封面以黑底紅字醒目的標題「Is God Dead?」對這個世代的思潮提出了一聲深沉的詢問。
在這種氛圍影響之下,我越來越確認,基督教如果想在華人群體中傳播,有兩大問題必須先加以面對處理:一個是華人的歷史與文化問題;另外一個就是當代思潮衝擊的問題。如果基督教對這兩個問題,不能妥善面對處理,想基督教在華人群體中落實生根,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。當年來自香港,在校園團契服事的宣教士蘇恩佩有一段時間住在我們家,曉風與我也都是《校園團契》雜誌的編委,我們三個人常徹夜圍坐,縱橫上下、談古論今。大家一致認為,如果《校園團契》雜誌自命為是當代知識分子的見證人,首先應當脫下機關報的性質,改名「校園」,以吸引知識分子的關注;進一步則應該在這兩個問題上有更多、更大、更深入的思考。
可是在編委同工會中討論時,第一個問題很快獲得共識,將「校園團契」雜誌改名為「校園」雜誌;但第二個問題則引起了一連串的討論,讀哲學的說當代思想文化這個題目涉及太多複雜層面,難於釐清;讀歷史的則認為基督教與華人歷史文化,恩怨情仇,糾纏不清,不易處理,最後因我多次發言,力陳利害,沒想到就由我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外行人,糊里糊塗地在更名為《校園》的雜誌上開始寫了兩個不定期專欄。我想,這都是上帝在我身上做的預備工作,因為這個緣故,我被迫有機會面對知識分子,面對大學學生的思潮,開始敏感地去關心那些議題;另外,我也不由自主的開始加入文字思潮的佈道領域,開始在《校園》雜誌寫有關教會歷史、當代思潮方面的文章。
專題演講,著作出版
當年東海大學有一批有名的人文學者,也有一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。為了面對這個情勢,東海基督徒每年在校內策畫舉辦「宗教加強週」講座,目的是希望與他們有對話宣教的機會。有一年他們竟然邀請我去擔任講員,那時我才三十出頭而已,經過禱告以後,我決定硬著頭皮壯膽去講。整整一個禮拜,我住在東海大學的招待所中,很用功的把過去收集整理的資料,重整分析,以尼采及海明威思想為主題,仔細思考,做了幾次專題演講。
後來我把那時所講的內容,加上在《校園》雜誌發表的幾篇文章,重整重寫以後,分別在香港、台灣結集出版了《現代人的痛苦》一書,沒想到那本書竟然得到熱烈回響,後來再增訂改版,出版了《突破痛苦的網》一書,竟然讓我得到了湯清文學獎的榮譽,實在非我始料所及。我們也曾組成一個小組,面對當時虛無反教、無神、無人的思潮,在校園書房出版專書,與以反駁。而我所寫有關華人教會歷史的專欄,經過重寫、改寫後,也在一九七○年交商務印書館出版《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化論文集》一書,開始了我在華人教會史領域的事奉。
而那時我們所屬由吳勇長老帶領的地方教會──許昌街團契(今日的林森南路禮拜堂),出了一個教會傳統刊物《信息》,主要內容是講道記錄。我們所帶領的那群學生團契卻覺得《信息》內容雖好,但太老式,編排方式也嫌陳舊。於是就由學生主導編了另一個刊物叫《靈聲》,最初是刻鋼版油印,後來改為排版鉛印,我與曉風因為是團契輔導,所以也一直參與了《靈聲》的編輯、發行及行政管理等工作。一九六一年開始太空發展,蘇俄太空人賈加林(Yuri A. Gagarin)首次進入太空,成功環繞地球一週返回後,人類的歷史正式進入太空時代,科學萬能的思想高唱入雲,我在《靈聲》寫了幾篇太空人的故事,使我關心的觸角及於科學與信仰的領域。我想這些裝備、經驗與訓練,都跟後來我能夠在中原及宇宙光從事教育、文化與歷史的服事有關。
全人理念的萌芽及成型
我在教會一直有機會作所謂的輔導,其實那時候台灣還沒有專業輔導的觀念,台灣的輔導系是很晚才設立的,大約在80年代。以前社會比較單純,沒有輔導的問題,大學中也只有少數幾個學校設有心理學系,中原大學算是最早設立心理學系的大學之一,劉家煜教授是中原心理系創系系主任,他曾經在宇宙光專欄連載發表很多有關輔導類的文章,並且結集成書,成為許多學校的教科書,暢銷多年。
他創辦中原心理系時,就有一個負擔,他覺得心理系的課程,其內容有文化與地域的關係,所以他曾親自來我家拜訪,邀請我在心理系開有關中國背景的社會學,以及中國歷史文化方面的課程,他希望中原心理系的學生,有好的中國歷史文化的傳統,而且所接受的社會文化理論,有中國本土化的色彩,他這種跨越時代的先見之明,後來臺灣的心理學界也陸續朝這方面發展。初出茅廬、年輕的我,在劉教授破格禮遇邀請之下,大為感動,以後幾年,在心理系教書,傾心盡力教導學生,鑽研各種學說理論,我要求學生分成小組,深入社會,依不同現象做研究調查,並且提出論文報告,所謂教學相長,因為這個緣故,使我更深涉獵文化社會問題,與同學之間也建立了緊密的師生關係,對我以後的服事產生了重大影響。
天、人、物、我
四個面向的全人理念
因為在中原心理系從事教學的緣故,我有機會接觸到社會學、心理學、教育界與許多專家學者,也有不少學生畢業後投身相關專業工作。後來台灣社會問題及青少年的問題越來越嚴重,一九六九年救國團決定成立「張老師」電話輔導,當時大學裡還沒有輔導系,也沒有輔導專業人才,找的人多半是政大教育系教育研究所的人,他們受到師大宗亮東教授的邀請,開始籌備電話熱線「張老師」輔導工作。那批籌備的人因為認識我,所以也聘請我擔任「張老師」的指導委員。當時只有澳洲有生命線,所以他們就參考那個模式做起電話輔導工作,輔導委員的責任之一就是出席每兩個禮拜辦一次的個案研討會,提供意見解決張老師所遇到的問題。
我記得有一次,某個「張老師」分享,有位求助者打電話來問說:「張老師啊,生命的意義是什麼?」他就回答:「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。」一講完,求助者很滿意,就把電話掛斷了。那位「張老師」很得意,說:「一句總統嘉言就解決了一個大難題。」把它當作成功個案來報告。我回應說這個問題應該沒有那麼簡單,那個學生所問的問題後面還有後續,我告訴他要密切注意。果然下次個案研討會時,他又把這個個案提出來說,那位學生又打電話來問:「張老師,你跟我說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,我聽了以後覺得很有道理,但是我回去以後,再仔細想想:我已經活得很沒有意義了,為什麼還要創造一個繼起的生命,讓他繼續沒有意義?」
其實那個學生所遇到的問題,正是一個追求生命意義的重大問題:「我是誰?」「我活著幹什麼?」「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?」「我為什麼要讀書?讀這麼多書要做什麼?」他的困惑在思考「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究竟在哪裡?」這些根本問題如果找不到答案,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。於是在第一屆「張老師」培訓班中,我提議開一門課:「張老師的人生觀與價值觀」。我認為這是一個前提性的根本問題,作為一個輔導者,如果他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是錯誤的,輔導技術越好,造成的結果必然會更糟。其實這不正是我們今天人類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嗎?當時這個培訓班因為是第一次舉辦,所以非常轟動,媒體都來採訪,結束以後,引起最多討論的就是這個講題。
在那次培訓講座中,我首次提及天、人、物、我四個面向的人生觀,那是後來全人理念中,天、人、物、我那個圓圖的概念第一次出現,大約是在一九七一年。後來讀路加福音二章51節講到耶穌十二歲時,就活出「智慧、身量、神和人喜愛祂的心都一起增長」的豐盛生命,心想,這正是中國人所追求的天、人、物、我、美滿圓融的生命境界,於是畫出了這個天人物我圓融美滿生命示意圖,因為我覺得中國人追求圓融美滿,而圓正代表圓融美滿,怎麼樣才能畫出一個圓呢?很簡單,天、人、物、我四個面向必須均衡發展,才能夠畫出一個圓來。這個觀念後來在宇宙光及中原大學逐步醞釀發展,終於形成了「全人」理念,面對後現代「單面向人(one-dimensional-man)的文化社會現象,「全人理念」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全新方向,逐漸被教育、學術、輔導及教會宣教工作,設定為努力奔赴的終極目標,這更是我們始料未及的一件大事,求主繼續帶領賜福給我們,向著標竿直跑,奔向終極,完成主交付給我們的大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