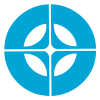那年我還很年輕,真的,眼睛特別明亮,兩頰紅潤潤的,照起鏡子,都覺得自己神采奕奕。
那是我踏入社會的第三年,從事的是「那個時代」相當熱門的電視影片製作,參與製作的名字,常出現在螢光幕上── 什麼?片尾那麼落落長(冗長)的一長排工作人員,誰會注意呢?怎麼沒有,我會啊,我自己就會注意啊,虛榮加上自我膨脹,老覺得只要出現一、兩秒,就全台灣都看到我的名字。
參與協談義工訓練
拿去虛榮和自我感覺良好,那時的工作型態,套句現在流行的話是:「上班打卡制,下班責任制。」寫完劇本、要出外景,剪好片子要配OS……我幾乎隨時都在工作,是的,「隨時」,夜以繼日,還包括主日,至於週間的團契,就連作夢都別想了。
就在信仰已接近枯萎的情況下,我有幸接受宇宙光協談義工的訓練,常缺席,但有機會一定去,上課時聚焦的不是諮商理論或技巧,而是每個老師的信仰,有時一句簡單到再不能的:「要多愛主一點啊。」都會惹得我熱淚盈眶。
在協談中心值班的那幾年,更是像夢像詩一般,美到不可思議,很多時間沒有個案,義工之間常談的是自己,自己的情緒、憂傷、擔心……在這過程中,我重新去整理自己的過去,一些持續存留並影響自己的陰影,至今那些伙伴的名字仍烙印在心版上:瑞玲、淑媛、恆序、春安……。唸著的此時,心也跟著溫暖起來。有趣的是,值班晚上,宇宙光會發餐費,每三個月領一次,明明當義工,拿到餐費還是特別開心,像撿到錢一樣。
奇異恩典,上帝知道我需要團契,值班的夜晚,可不就是深度心靈之旅的團契嗎?還有餐費,恩上加恩。
諮商中心結束義工,和我進入救傳幾乎同時,林哥不時到救傳電視部錄影,幫他或別麥克風,或討論訪談內容,數度我差點脫口而出:「林哥,我曾在宇宙光當過義工呢!」
所幸沒有,因為很快的我就發現,曾在宇宙光擔任義工的,如過江之鯽,簡直不可勝數。
上帝恩典的介入
二○一一,辛亥百年史詩劇場,當時我的主管吳錡受邀擔任導演,節目腳本的撰寫就落在我頭上──多意外的機緣,我又可以當宇宙光的義工了。
當義工,是去回味年輕時那種不求回報的熱情,是感受那種功利社會已然消失的不計代價、放膽去做的傻子精神,我真真覺得林哥是我看過最浪漫主義的人,他幾乎無視於任何近在咫尺的困難與挑戰。
嚴格說來,第二回合的義工生涯,只持續了一個禮拜,比較密集的去看一些資料,然後把它轉化成文字。但我依舊是那個被恩待的人,彩排時溜進去,然後伸手去抓不知誰洗切好的水果;演出時照樣先跑到後台,自覺與演出團隊有特殊關係,逕自拿個便當再說。
倒是史詩劇場演出時,怎麼也輕鬆不起來,當紅幕冉冉升起,愛心合唱團和諧的和聲響起,我眼眶就這樣慢慢的熱了起來,就一個台北街頭隨手一揀就一大把的文字工作者來說,何等榮幸,我的文字如此被使用、被呈現!
我忽然發現,我從來不是宇宙光的義工,相反的,上帝透過宇宙光在不同階段,造就我、激勵我。
宇宙光之於我,是上帝恩典的介入,看起來我投入,事實上我是那領受最多的。
奇異恩典,恩典奇異。